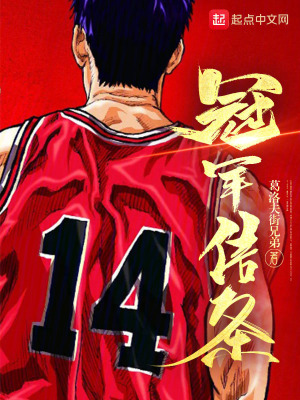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玉皇大帝转世之长生诀续! > 第423章 玉帝张兴东感悟这基础设施基础工程中最重要的是兴修水利(第1页)
第423章 玉帝张兴东感悟这基础设施基础工程中最重要的是兴修水利(第1页)
天庭水利记
紫霄宫的玉阶被连日的暴雨冲刷得发亮,玉皇大帝张兴东望着案头堆积的奏章,眉头拧成了绳。最上面那本《三界水患录》上,“黄河决堤,良田尽毁”“珠江泛滥,溺亡三千”的朱批旁,还沾着凡间百姓的血泪。
“陛下,”太白金星捧着拂尘的手微微发颤,“东海龙王降雨失度,致使凡间洪涝成灾;而西域旱魃作祟,良田龟裂,百姓易子而食。天庭的水利仙官只会筑坝堵水,三千年了,治水之法竟毫无长进!”
张兴东望向殿外,南天门的梁柱上还挂着未干的水渍——前日天河倒灌,若非天兵拼死抵挡,凌霄宝殿险些被淹。他忽然想起乾坤镜里的景象:凡间的三峡大坝如巨龙横卧,拦住滔天洪水;南水北调的水渠像银色的绸带,将长江水引向干涸的北方;实验室里,人们用“水文模型”预测洪水,精准得如同未卜先知。
“朕要去凡间看看。”他周身的帝气悄然收敛,化作一身粗布蓑衣,腰间的玉如意换成了丈量土地的标尺,“看看真正的‘治水之道’,究竟是什么模样。”
太白金星急道:“陛下三思!水利乃天定,岂容凡人妄改?治水当靠龙王降雨,哪能靠铁石筑坝?”
“若天道不公,水患不绝,那这‘天定’便该改改。”张兴东扛起墙角的铁锹,“就说朕闭关悟‘润下之道’,一应事务由你暂代。”
话音未落,他已化作一道清风坠向凡间,落在黄河岸边的“利民水利站”外。
正是汛期末尾,河岸边却不见想象中的狼藉。几个穿蓝色工装的人正站在堤坝上,用“全站仪”测量沉降,远处的“清淤船”正将河底的泥沙吸上岸,堆成整齐的土丘。堤坝内侧的“生态护坡”上,芦苇丛生,几只水鸟正在浅滩觅食,与坚硬的混凝土相映成趣。
“老先生是来视察的专家?”
清脆的声音自身后响起,张兴东转身,见是位戴草帽的姑娘,裤脚卷到膝盖,小腿上沾着泥点。她手里拿着个巴掌大的仪器,正往堤坝上贴,仪器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波形。胸前的工牌写着“王晓晓 水利工程师”,晒黑的脸上嵌着双明亮的眼睛。
“路过此地,见这堤坝稳固,特来请教。”张兴东目光落在那仪器上,“这小玩意儿能比河伯的‘测水灵珠’还准?”
“这是‘渗压计’,能测堤坝的渗水情况。”王晓晓笑着扬了扬手里的平板,“您看,这是整个河段的‘数字孪生模型’,哪里有管涌、哪里会沉降,电脑上看得一清二楚,比肉眼观察早三天发现隐患。那边的‘泄洪闸’是智能的,水位超过警戒线会自动开启,不用再靠人盯着。”
她引着张兴东走上堤坝,脚下的混凝土路面平整坚实,每隔百米就有一个“监测桩”。“这堤坝是‘百年工程’,地基打了三十米深,用的是‘高压喷射注浆’技术,能抗百年一遇的洪水。我们还在两岸种了防护林,既能固土,又能净化水质——治水不能光堵,得疏堵结合,还得跟自然交朋友。”
张兴东抚摸着冰凉的堤坝,忽然想起天庭的“天河堤坝”——三千年了,还在用夯土筑成,每逢汛期便要仙兵用仙法加固,稍有松懈便溃堤。上次天河决口,淹没了下游三座仙岛,至今还一片荒芜。
“姑娘觉得,治水的根本是什么?”他忍不住问道。
“是让水听话,更要让人水和谐。”王晓晓指着远处的灌溉渠,“您看,这‘引黄入灌’工程,把洪水拦住,变成灌溉的活水,干旱时能浇地,洪涝时能蓄洪。我爷爷说,以前黄河三年两决口,百姓逃荒要饭;现在修了水库、堤坝、水渠,两岸成了粮仓,这才是‘水利’的真意——不是跟水斗,是跟水合作。”
正说着,监测中心的警报突然响起。屏幕上显示上游支流出现“管涌”,水位正以每分钟两厘米的速度上涨。王晓晓立刻拿起对讲机:“立刻启动应急预案!调抽水机到管涌点,同时组织人员用沙袋围堵,我马上到!”
她跳上越野车,还不忘对张兴东喊:“老先生要是感兴趣,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堵管涌!”
车在堤坝上飞驰,张兴东看着窗外掠过的防护林,忽然想起当年大禹治水——三过家门而不入,靠的是“疏”而非“堵”,可天庭的仙官却忘了这个道理,只知用蛮力挡水。就像刚才太白金星说的“天定”,实则是不思进取的借口。
管涌点已围了不少人,抽水机正轰鸣着排水,几个工人正往管涌口填“反滤料”。王晓晓跪在泥地里,用手摸着水流的方向:“不是单个管涌,是一串!从这里到那边,至少有五个点,快调‘地质雷达’来探测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