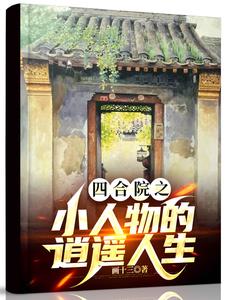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昨夜星辰昨夜风1 > 第8章(第3页)
第8章(第3页)
“你在干吗?”
初醒的声音带着点淡沉的沙哑,像刚出炉的酥糖,软糯即化,毫无疑问,我能在此时此刻这么悠闲地联想,就说明这一声对我而言是多么大的心灵冲击。
我轻拍了拍他的脸,柔声道:“这是个梦。”
程靖夕在面无表情地看了我片刻,然后抬起搭在我腰上的手贴到我脸上,捏起一块肉,用力一扭。
“啊,好痛!”我拍掉他的手,捂着脸委屈地瞪他。
他抬抬眼皮,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
揉脸的手突然静止,我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,那根本就不是梦!
我的心脏顿时跳到了嗓子眼,仿佛有无数个小人高举“怎么办”的大字牌狂奔而过,好在我定力十足,眨了眨眼,低沉着嗓子对他道:“你在做梦。”
然后,一个大前跃跳起来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去。做这个动作前,是凭着我对自家的熟悉程度而言,我很有信心,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会儿太过紧张,急于跑路,我绊倒多次,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出去。其间,还差点认错门撞进公卫,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
好不容易跑到别墅外面,鬼使神差地回头一望,看见穿着白色睡衣的程靖夕正倚在阳台上托着腮的身影,他对我招了招手。
我哀号一声,捂着脸落荒而逃。
一路狂奔回梨园,我一头扎进被子里,想想还是觉得丢脸,跳起来又怄又恼地将脑门往墙上撞了几下。头被撞得生痛,可见我自知这个脸丢得有多大。
但经路上凉风一吹,以及几下大脑的撞击,我终于可以冷静下来,细想一下这个事的诡异之处。昨夜最后的记忆,我记得是在歪脖子大树上,所以,就算我睡着了,也该是睡在树上才对。可怎么醒过来时,却是和程靖夕同在一张床上?
况且,我还记得,我离开时,程靖夕是在沙发上睡着的,还是我给他盖披的毯子。将这两个记忆连在一块儿,三天后,我终于绞尽脑汁地拼凑出了两种可能。
一是程靖夕看见窗帘拉得不那么整齐,他就顺便那么一整窗帘,然后自然就看见了窗外的我。二是我在树上睡得迷迷糊糊时被冷风吹醒,就半昏迷状态自行爬回去,往熟悉的床垫上一躺,呼呼大睡。当然了,这两种情况都是以程靖夕在沙发上睡完一觉回到房间的前提下。但以我对程靖夕的了解,一般第一种情况,他不叫保安都是大慈大悲了,可能看着过去的情分上给我留点脸面,就毫不犹豫地扣死窗户,拉上窗帘,装作没有看见我。
所以,综上所述,能够说服我及大众的,就只有第二种情况了。只是不知道,昏睡的那几个钟头里,我有没有凭着本能对程靖夕做什么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