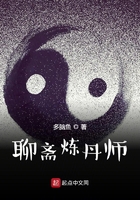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[完结]《狱门关》作者:Yankee Doodle(np) > 第8章(第1页)
第8章(第1页)
这是狱长想出来的玩法,岑郁被强制坐在狱长的腿上,狱长的阳物就深深捅入他的后穴。狱长一边捻着他的乳珠,一边在他身上释放了两轮,粘稠的精水与肠液顺着岑郁股间溢出。
大概是不够尽兴,狱长想了很久以后,让他的秘书拿来了一副电钻,换上一根五毫米粗的钻头,通了电,往岑郁的指甲盖上钻去。
岑郁这时候已经在狱中受了一年的折磨,对疼痛的耐受力强了很多,一般的鞭打、群殴皱皱眉就忍过去了,而今天这食指钻心的痛楚激的他瞬间迸发出痛苦的嘶吼,浑身肌肉颤抖着,而他的后穴也骤然收紧,狱长这才发出一声快意的长叹。
那天他的双手被钻了十五个孔,指尖与手背布满血洞,嘴里被塞了狱长的内裤,只能发出呜咽声。
狱长满足以后,岑郁侧躺在地上,蜷起身子,双手痛苦的攥紧又松开。接着,已经面无血色的他又被拖到一间监室里。
狱长说,要服侍到这里的每一个囚犯满意,才可以离开这里。
这些欲望被压抑太久的男人已经在他身上释放过三轮了,兴高采烈的探讨还有什么新花样可以玩。
留给岑郁喘息的时间并不多,很快他的口中与后穴又被填满,连尿道都有囚犯恶意的伸进手指抠挖。
他的唇舌忍着呕吐感,机械的吮吸口中腥臭的物体,快感与疼痛都麻木了,只剩下绝望的感觉。
岑郁闭上了眼,眼角有些湿润。
再度睁开眼时,却是陌生的场景。不是监狱里高悬着的刺眼的白炽灯,而是雪白的天花板。
浑身的病痛也在慢慢的苏醒,每个关节、每个毛孔都仿佛被撕扯着。
双手的疼痛尤其尖锐,被电钻钻过以后,没有及时的医治,他原本修长洁白的双手变得畸形怪异,指节扭曲,布满伤疤,更是僵硬无比,几乎成了一对摆设,稍微动一动就钻心的疼。
在监狱里,他唯一有用的部位就是身上的几个洞,双手显得可有可无,便也无人在意是否残废。
身体上插满管线,连着几台仪器。周围很安静,只有仪器运转的声音。
这里不是黑山监狱的医务室,那里只有几张染满污渍的木床板,比药品更齐全的是束缚工具。
这是他久违的、监狱外的人间。
岑郁花了很长时间,才想明白自己现在是在一间医院里。他没有精力去想前因后果,脑海中浮现的是监狱中的桩桩件件与少年时遭受的欺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