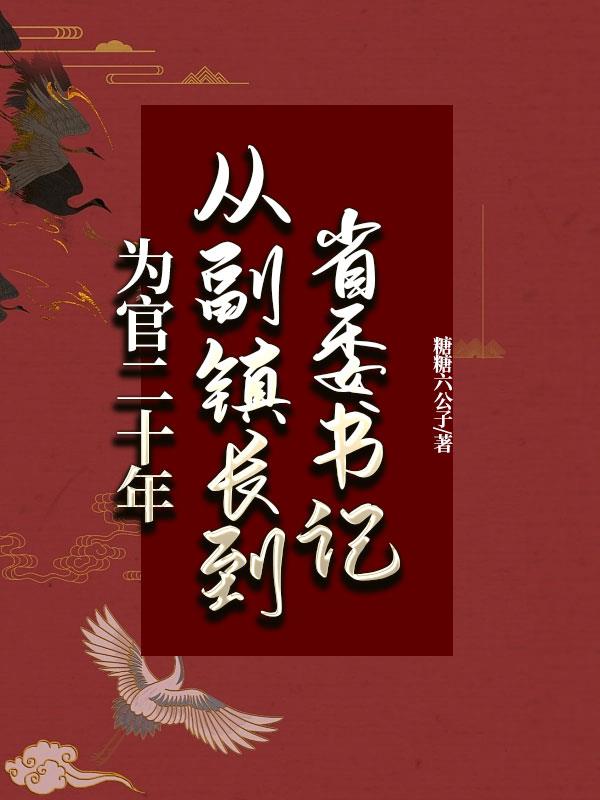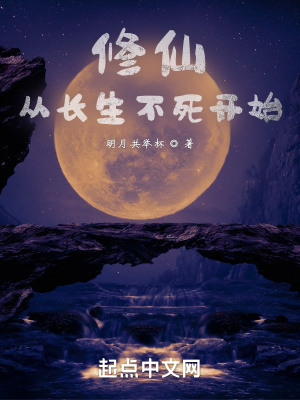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她为何总被大佬创飞(无限 NP) > 北荒1970(29)(第2页)
北荒1970(29)(第2页)
付了饭钱,王许拽住收拾碗筷的服务员,递了支烟:“大兄弟,问个事儿,这县城除了国营照相馆,还有没私营的?”
服务员叼着烟斜睨他:“你开啥玩笑呢?这年头啥不是公家的?”
“咱是兵团的,”王许压低声音,指了指李良宵几人,“革命战友,过些天要分别了,想拍张照留个念想。可国营相馆那效率,少说等一个月,咱想两三天就拿到。”
服务员眼睛一转,目光在李良宵身上打了个圈,忽然凑近了些,神秘兮兮地笑:“这不巧了!相馆照相的师傅是我二舅。只要这姑娘肯给相馆拍几组样板照,你再报我刘建军的名字,一周之内拿相片,保准没问题。”
照相馆藏在县城主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。这年月,照相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件稀罕事,来的多是追逐新鲜的年轻人,或是有些家底的人家。
推开门,一股混合着显影药水、陈年木头和灰尘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。室内光线比外面更暗,一盏蒙着灰尘的白炽灯悬在屋顶,勉强照亮一方天地。
墙上挂着几幅泛黄的样板照:穿军装的男女并肩而立,背景是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语;戴红领巾的孩子举着语录,笑得露出豁牙。
最里头的黑布罩着一台老式座机相机,镜头像只圆睁的眼,对着屋子中央的红绒布布景。
照相的老师傅正用麂皮擦镜头,抬头瞧见李良宵,眼睛倏地亮了——这姑娘眉眼精绝,皮肤在北荒的寒风里竟还白里透红,活像朵绽在雪峰之巅的青莲。再瞥见赵延锋,老师傅更乐了,这小伙子身姿板正,眉眼冷峻,往那儿一站,自带股凛然英气。
王许上前,堆着笑报了饭馆服务员“刘建军”的名字,又说明了来意。
刘建军是我外甥!”老师傅惊喜地一拍大腿,他直指李良宵和赵延锋;“只要这俩娃配合我拍几张样片,别说两三天拿相片,加急费都免了!”
众人赶紧整理着装。张小兰帮李良宵把帽子扶正,赵延锋拽了拽棉袄下摆,王许则偷偷把头发揉得更蓬松些。
“先拍集体照!”老师傅搬来木凳,“后边俩小伙站着,前边俩姑娘蹲下!”
赵延锋和王许往后退了半步,肩并肩站定。李良宵和张小兰蹲在前头,冰凉的地面透过棉裤往上渗。赵延锋却忍不住嘴角微勾——王许正偷偷往他身后缩,脚尖踮着,想显得自己高点。
“咔嚓!”镁光灯骤然亮起,带起一团硫磺味的白烟,瞬间将四人的身影定格在底片上。
接着拍三人照。李良宵站中间,王许往她左边一靠,胳膊差点搭到她肩上,被赵延锋不动声色地撞开。赵延锋站在右边,离李良宵半尺远,却在老师傅喊“靠近点”时,极轻微地往她那边倾了倾身。
“明月……”张小兰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和祈求,“能……能跟我单独照一张吗?”
这一个月来,张小兰小心翼翼的靠近、欲言又止的关切、以及那直白得近乎灼热的目光,李良宵再迟钝也能感觉得到。只是,对于这份异常的情愫,她只能装作浑然不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