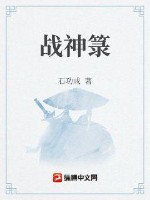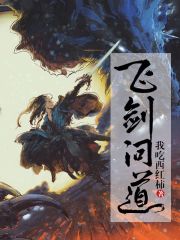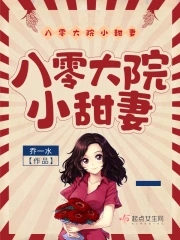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快穿局女员工 > 第329章 县学(第3页)
第329章 县学(第3页)
林乔仰头望去,青瓦与芦苇交错排列,在落日余晖中泛着金色的光芒,确实比原先纯瓦顶更显别致。更关键的是,这种创新设计节省了近三成的瓦片费用。
当晚,林乔在油灯下重新核算账目。由于精打细算和族人的无偿劳动,原本捉襟见肘的二十两银子竟有了结余。
"007,计算一下,若保持这个进度,工程结束后我们能赚多少?"
"初步估算,扣除材料费和必要开支,净利润约五两银子。"系统回答,"但更大的价值在于社会声誉的提升和人际关系的拓展。"
林乔点点头。确实,这几天他已经结识了好几位县里的人物:木材商刘掌柜、砖瓦窑李老板,还有几个常来查看进度的县学士子。这些都是宝贵的人脉资源。
第十天,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张明远带着几位乡绅来视察,其中就有周员外。那是个五十多岁、身材发福的男子,穿着绫罗绸缎,手指上戴着硕大的玉扳指。
"这楼修得倒快,只是用芦苇代瓦,未免太寒酸了吧?"周员外摸着胡子,语带讥讽。
不等林乔回答,张明远便道:"周兄有所不知,这芦苇经过特殊处理,防水防蛀,比寻常瓦片更耐用。且交错排列,别具一格。"
其他乡绅也纷纷称赞这种创新设计。周员外碰了个软钉子,脸色不太好看。临走时,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林乔一眼,"林教习好手艺,只是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"
这话里的威胁意味不言而喻。林乔面上恭敬,心中却已警惕——周家对林家的打压,恐怕还会升级。
工程过半时,林乔的认真负责赢得了张明远的彻底信任。一天傍晚,老教谕特意留下他喝茶。
"林教习,老朽观你言行,不似寻常农家出身。"张明远捋须道,"可曾读过四书?"
林乔心中一凛,谨慎回答:"家父在世时请过西席,学生粗通文墨。"
"哦?"张明远来了兴趣,"《大学》首章,背诵来听听。"
林乔从容背来,不仅一字不差,还能讲解其中精义。老教谕越听越惊讶,最后拍案道:"奇才!逃荒路上竟藏着这等人才!"他沉吟片刻,突然道,"林乔,你可愿拜我为师?"
林乔一时愣住。张明远虽是县学教谕,但早年曾中过举人,在青山县文坛地位颇高。能拜在他门下,对提升社会地位大有裨益。
"学生...学生不敢高攀。"他连忙起身行礼。
"不必过谦。"张明远笑道,"我平生最惜才。你若愿意,待工程结束后,行个拜师礼便是。"
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!林乔当即跪下,行了半个拜师礼,"蒙先生垂青,学生铭感五内!"
消息传回窑场,族人们欣喜若狂。读书人在古代地位崇高,有了这层关系,林家再不是任人欺凌的流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