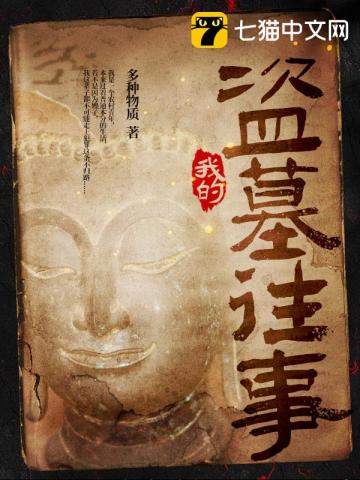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【82】《公主玉河》作者:俞嵬 > 第53章(第2页)
第53章(第2页)
钟鼓旗随之反应过来叫他含在嘴里的是什么,微怔钟玉河的骤然孟浪以后,他也不觉羞耻,反倒试着张开喉咙的软肉去裹钟玉河的肉头。
咸咸的味道在他嘴里发散,他猛地一吸,钟玉河的手就软了似的垂下来,又耐不住似的紧紧地抱着他的头。
钟鼓旗没有试过这种感觉,只知一个劲儿地舔舐深含,没有几分技巧的快慰,反倒叫钟玉河红着眼角根本站不住脚。
被迫性的泪水泌出钟玉河的眼眶,他压低着嗓音嗯嗯啊啊地叫唤着,抱着钟鼓旗头的手臂越来越紧。
钟鼓旗也不觉得恼,反倒觉得分外满足,猛地一嗦。
钟玉河的腿骤然一软,钟鼓旗眼疾手快地抱住他,将他平放在地面,却不打算放过他。
就算钟玉河受不住地抵着小腿后退,钟鼓旗还是把着他的脚踝,深埋在他胯下深吞着。
一时间洞里只有啧啧水深,钟鼓旗喉结吞咽的声响,还有钟玉河压紧的叫唤呻吟。
最后一个深吞,钟玉河紧紧勒着钟鼓旗的脖颈,濒死似的尖利地一叫,就有白色的蓬蓬的液体从钟鼓旗嘴角溢出。
钟玉河被吓到似的猛然一抽,飞溅的白浊就有些落在钟鼓旗的脸上。
顺着那道凌厉的疤痕凹陷,缓慢地向下流动着。
还有些覆在钟鼓旗的眼睫上,他一眨眼,就啪嗒一团滴回他的嘴唇上。
钟玉河睁大着眼,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些差异,有些胆怯地往后退着。
却被钟鼓旗一把拉住脚踝,漆黑地蒙着灰雾的眼睛幽幽地顶着他。
钟玉河以为他是要发作,却听咕嘟一声,钟鼓旗竟是当着他的面,将嘴里的蓬蓬的一团尽数咽下。
钟鼓旗盯着钟玉河斑驳的下身,不怒反笑,眉眼弯弯还挂着星点的白浊,却是比任何时候都要怕人。
张口说话间露出通红的口腔,是叫钟玉河方才猛烈的抽插磨破的的血口子。
“钟玉河,还说你不欢喜我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