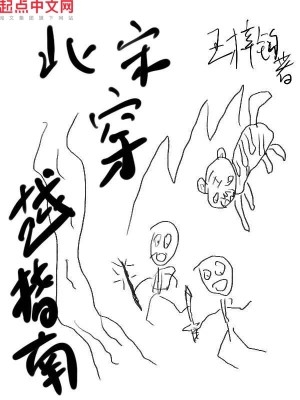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《橘子汽水》by阿司匹林(完结1v1) > 第94章(第3页)
第94章(第3页)
一下比一下重,水声也越来越响,汁液顺着泛红的大腿根颤巍巍地往下淌,在床单上印出一片深色的水痕,快意频繁地冲刷着大脑里脆弱的防线,神经末梢都有些迟钝,但依然抵抗不了一波一波往上涌的浪潮。
她颤抖着哭出声,几分钟就承受不住,无力地栽进枕头里。
他俯下身,炙热的胸膛贴着她的后背,大手掰过她的脸凶狠地亲吻,腰腹下顶撞的力道没有丝毫要减弱的势头,甬道内壁疯狂收缩、痉挛,热潮凶猛地袭来,她有种会在这激烈的快感里窒息的错觉。
她在求生意念的催动之下试图挣扎,当然只会是徒劳。
热潮从四周笼罩过来,他的脸埋在她颈间拱动,蹭到哪里都是湿湿的,他摸到她满脸泪水,喘息声里混着极为可怜的哭腔,下面也缩得很厉害,绞得他发疼,额头的汗滴在她身上,直到听到满意的之后才不再抵抗那股要命的快意。
她在眼前炸开那束白光前一秒对他说:程遇舟,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了。
……
他们下午才去医院。
程遇舟说这几天不会带周渔去其它地方,就真的没有带她去,他要延续她对南京的新鲜感和好奇,这次主要是熟悉他的家,下次有下次的安排。
言辞和程延清也在医院。
护士来给程挽月输液,病号服从袖口卷起来,皮肤上全是一块一块的乌青,程延清在护士扎针的时候说笑话逗她。
很疼,疼得难以忍受,程挽月忍得嘴唇都白了,她喜欢病房里有很多人,这样热闹一些。
“阿渔,言辞,你们要回去上课了吗?”
“明天才走,”周渔坐到病床边的椅子上,手伸进被子里,轻轻握着程挽月的手,“我晚上在医院陪你。”
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,好想吃学校旁边那家炸串,我高三下学期好好学习了,都没吃几次。”
“那家店的老板回老家帮儿媳妇带孩子,门面转让给别人开粉面馆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