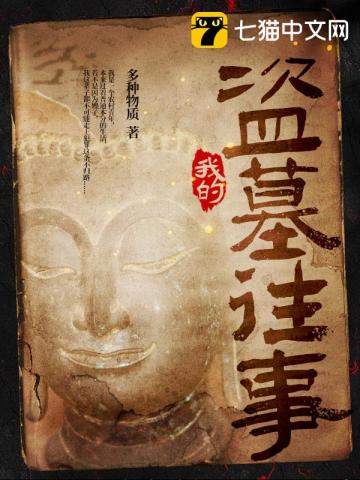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《金穗》作者:好玩好玩 > 第189章(第1页)
第189章(第1页)
我自己经历过许多绝望时刻,习惯于自我鼓励,但别人嘴里的到底不一样,它就像“一定会好起来的”的回音“对,没错”,有一锤定音的鼓舞力量。
因此到了末了,本想畅谈的营救计划变得无从说起。
他把佛珠搁到一旁桌子上。“我这小徒弟就像只野猴子,生存本事可强了。”他闲聊似的来了一句。
他不会劝我顺其自然吧?那可不行,我意已决!
“你还爱他吗。”他突然问。
“爱。”
“那很珍贵!”他欣赏地赞叹。
我害羞地笑了笑。
他说起了他的过去。“家国众生的课题太大了,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,爱情是很可贵的。你别看我是个出家人,我知道这种感情的珍贵。它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相互理解,信任,着想,付出,为了对方变得更好。这难道不伟大吗?我出家的契机是我爱人过世了,我不能再给另一个人这样的偏爱,于是我选择了平等地去爱。”
天呐,唐师傅他居然是纯爱战士!
我惊讶得眼珠瞪起。
“所以,我这帮徒弟谁要是动了凡心,我是支持还俗的。因为他们的爱有轻重了,不再平等,那就不合适再当和尚了。爱没有对和错,应该不应该。当然,我说的是爱,不是欲,前边那个和继母纠缠不清的小施主,他们那是欲。我在清规戒律上没那么严格,违反教义的人,他们只是不能胜任原本的角色了。但有一点,我放人出去的时候,我希望他好好对待他的新角色。”
“你们也是。”他最后说。
我走出佛堂前,唐师傅给我看了里面那张桌上霍双小时候调皮捣蛋留下的刻字。
“只念经不玩耍,聪明又又也变傻”。
我还以为会刻早字呢。
这天吃晚饭前,接到了程奔秘书打来的电话。
我在后院的院门口接电话。院门正对着饭堂,右手边是唐师傅的小佛堂后门,整间院子不足300坪,舒怀意就立在饭堂前的石榴树下,定定地望着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