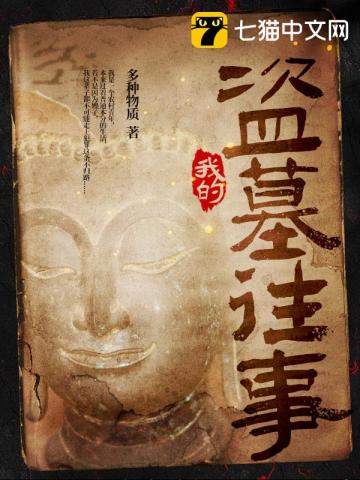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慕容世家之燕国传奇 > 第159章 岁的战神慕容垂依然所向披靡(第2页)
第159章 岁的战神慕容垂依然所向披靡(第2页)
“这招叫‘雪割’,”慕容垂的声音冰冷如铁,“是我十五岁在辽东雪原杀出来的刀术。”他反手一刀,刀光如月牙般划过,拓跋虔那颗不可一世的头颅便滚落在地,眼睛还圆睁着,仿佛至死都不敢相信,自己竟会死在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刀下。
平城城门轰然洞开时,慕容垂正站在拓跋虔的尸身前,剧烈地咳嗽着。他看着城中三万北魏部落百姓跪伏在地,看着那些曾在参合陂被俘的燕军士兵哭着扑过来,突然觉得手中的刀无比沉重。“传我令,”他对慕容农说,“善待这些部落百姓,给他们粮种,让他们开春耕种。拓跋虔的家眷,一个不杀,送到中山为质便可。”
慕容农一怔:“父亲,拓跋虔杀了我们多少弟兄?这些士兵哪个不是血海深仇?”
老人望着远方的云中川,那里曾是拓跋部的发源地。“杀得完吗?”他轻轻擦拭着“破虏刀”上的血,“我十三岁那年,在辽东杀了段部的王子,结果段部与慕容氏仇杀了三十年,死了多少人?今日杀了拓跋虔的家眷,明日拓跋珪便会屠尽我们的宗室。冤冤相报,何时是头?”他顿了顿,看向那些正围着拓跋虔尸体嘶吼的士兵,“告诉他们,血债已偿,但参合陂的弟兄们,更想看到燕国的太平。”
慕容轩扶着慕容垂登上平城西门的残垣时,老人剧烈地咳嗽起来,一口血喷在冰冷的城砖上,迅速冻结成暗红的冰。他望着脚下溃逃的北魏士兵,突然低低地笑了,笑声里带着无尽的疲惫:“阿轩你看,只要我还能握住刀,这天下就没人能赢我。”
可当他的目光扫过城中的断壁残垣——那是北魏士兵撤退时纵火留下的痕迹,焦黑的房梁下还挂着半具孩童的尸体,被冻得硬邦邦的——笑容突然僵住。他想起十三岁那年,在辽东战场斩下第一个敌人首级时,父亲拍着他的背说“这一刀是为了让辽东百姓安稳吃饭”;想起枋头之战后,苻坚的降兵跪在雪地里哭喊“求大将军给口粥喝”;想起自己亲手为参合陂死难者立的无字碑,碑石上的冰缝里还嵌着未干的血……
“赢了又如何?”老人的声音轻得像雪落,“十三岁到七十岁,我杀了五十六年的人,砍断的头颅能堆成一座山。可你看这天下——”他的手划过眼前的废墟,“长城脚下的尸骨还没烂透,黄河岸边又堆起了新坟。当年我在长城上跟扶苏公子说,总有一天要让百姓‘夜不闭户,路不拾遗’,如今倒好,连我慕容家的都城都快保不住了。”
慕容轩握住他冰冷的手,那只曾挥舞“破虏刀”横扫中原的手,此刻竟抖得像片落叶。他想起长安城外那棵老槐树,想起蒙恬自刎时染血的白袍,想起扶苏公子临终前那句“若武力能救天下,秦何至于此”——原来两世轮回,他们拼尽全力追逐的胜利,从来都不是答案。
“叔父,”慕容轩的声音哽咽,“您已经做得够多了。当年您带着残部从辽东杀出,在枋头以少胜多,灭西燕、破苻秦,让慕容氏在乱世中站稳脚跟,已经护了多少百姓免遭屠戮?”
慕容垂摇摇头,望着北方的天空,铅灰色的云层里仿佛藏着两世的遗憾。“不够啊……阿轩你记着,当年在长城上,我跟扶苏公子立过誓——要让天下人‘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’。可你看现在,”他指向城角蜷缩的孤儿,那孩子正抱着冻僵的母亲尸体哭嚎,“这就是我用一辈子胜仗换来的天下?”
他突然剧烈地咳嗽,咳得弯下腰,半晌才抬起头,眼中竟有了泪光。“我终于明白了……蒙恬为什么要自刎。他不是输给了赵高,是输给了自己——以为握着刀就能护住一切,最后却连公子的性命都保不住。我慕容垂打了一辈子胜仗,却连燕国的根基都守不住,连‘太平’两个字怎么写,都快忘了。”
老人从怀中掏出那串断裂的紫檀念珠,将碎成两半的“合”字珠放在掌心,轻轻合拢。“阿轩,我这把老骨头快熬不住了。这天下,终究要交到你们手里。记住——”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无比坚定,仿佛两世的执念都凝聚在这一刻,“靠刀枪赢来的,迟早会被刀枪夺走。真正的太平,不是杀出来的,是熬出来的——熬到百姓不再想打仗,熬到孩子们不知道刀是什么,熬到长城上的烽燧再也不用点燃……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他将念珠塞进慕容轩手中,指尖的温度透过木头传来,带着两世未凉的热血。“你和婉清,要替我,替蒙恬大将军,替扶苏公子,把这条路走下去。别再像我这样,赢了所有的仗,却输了最初的梦。”
当燕军前锋逼近云中川时,草原上的部落正在篝火旁议论纷纷。“慕容垂真的来了!”一个白发老者颤抖着说,“当年他在枋头,单骑冲阵,苻坚的箭射在他的甲胄上,竟全被弹开——那是天神护体啊!”年轻人们却面露惧色:“可拓跋虔将军都死了……听说他的大槊被慕容垂当作战利品,就插在平城城楼上。”
拓跋珪在盛乐宫中,看着手中拓跋虔的首级,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帐外传来草原诸部的异动——贺兰部、纥突邻部都在悄悄派使者去燕军大营,连他最信任的叔祖拓跋纥罗,都在帐中私藏了慕容垂的画像。“撤!”他猛地将首级扫落在地,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恐慌,“退回漠北!等这老东西死了再说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