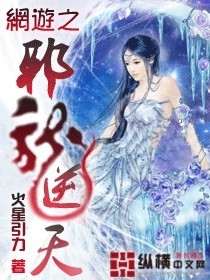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天造地设(公路,1v1) > 83纵情声色(h)(第2页)
83纵情声色(h)(第2页)
“类似于一些国家的服兵役?”邬锦上了床,自动睡一边,没一会,床榻另一边有所陷落,他上了床,钻进同一张被窝里,长手一伸掀灭了灯。
“服兵役这个说法就严肃了。”杨侜在黑暗中想了想,“类似于成年礼吧,决定权在自己,没有法律法规要求。”
邬锦“噢”了一声,“那你当过和尚?”
杨侜:“当过一个月。后面还俗了。”
邬锦侧眼:“有照片吗?”
“干嘛?”
“不可以看吗?”
她没说自己好奇想看,直接反问,杨侜只好说:“我翻一翻,不知道还在不在。”
他当和尚时已经二十多岁了,年龄算是比较大的,印升荣当时送他去寺庙,目睹了他剃度过程,期间给他拍过一张照片。
细想了下,那是好几年前了,好在杨侜没换手机,平时的照片也并不多,手指在屏幕上滑动了几下便在图库里找到了先前保留的照片。
那是一张他已经剃度了照片,身穿藏红色长袍,脚踩人字拖的木屐,注视着前方的一池绿水,他站姿挺拔,并未弯腰低头,甚至是习惯性的防御姿态,眉目是从未改变过的锋利,怎么看都挺违和的,只有那黑沉的眸子在身后远处高大菩萨的衬托下有所柔和。
邬锦凑过去,拿过手机放大:“还挺好看的,为什么还俗?”
别人都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,他倒好,脱下袈裟当杀手。
杨侜一本正经地回答:“可能是为了操女人吧。”
“……粗俗。”她骂他,把手机扔到他胸口翻了身背对着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