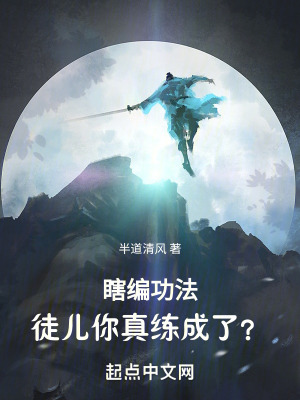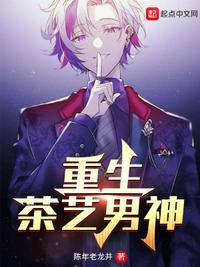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打造最强边关 > 第775章 谷满安阳(第1页)
第775章 谷满安阳(第1页)
农人们七嘴八舌,脸上的皱纹里都盛着笑意。叶明听着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当初他从现代带来的那些农业知识,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。
日头渐高,打谷场上的声音越发密集。叶明告别农人,循声而去。打谷场中央,十几个壮汉正挥舞连枷,有节奏地拍打着晒干的稻穗。金黄的谷粒从稻壳中蹦跳出来,在阳光下像一粒粒碎金。
"大人来试试?"一个赤膊汉子递过连枷。
叶明接过这简单的农具——两根木棍用皮绳连接,挥动时上面的木棍会旋转拍打稻穗。看起来容易,实际操作却需要巧劲。起初他掌握不好力度,不是打空就是太重。周围的农人善意地笑着,耐心指点。
渐渐地,叶明找到了感觉。连枷在空中划出弧线,"啪"地一声脆响,稻穗应声脱粒。这种原始的劳作,竟有种说不出的畅快。
"大人打得不错!"赤膊汉子竖起大拇指,"来,喝口茶歇歇。"
场边支着口大铁锅,锅里的老荫茶冒着热气。叶明接过粗瓷碗,茶水滚烫,带着淡淡的苦涩,却意外地解渴。
正喝着,一阵欢快的笑声传来。几个农家少女挎着竹篮,正在捡拾散落的稻穗。她们灵巧的手指在稻草间翻找,不时举起一粒特别饱满的谷子,像找到宝贝似的欢呼。
"这叫'拾秋'。"老屯长不知何时站在了叶明身后,"老规矩,打谷场掉落的穗子,谁捡到归谁。"
叶明点点头。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传统,比任何严苛的律法都更能体现农耕文明的智慧。
日头偏西时,叶明来到晒谷场。偌大的场地上铺满了金黄的稻谷,几个老人手持木耙,慢悠悠地翻动着,让每一粒谷子都能晒到阳光。谷粒在木耙下发出细微的沙沙声,像是大地轻柔的叹息。
"晒三日,就能入仓了。"管仓的老吏捧着账本,喜滋滋地报告,"东屯已经缴了一千二百石,西屯九百石,北屯最多,一千五百石还有余..."
叶明望着晒谷场上金灿灿的一片,恍惚间觉得整座安阳城都沐浴在这金色的光辉中。粮仓将满,百姓无忧,这不正是为官者最大的心愿吗?
回城路上,叶明的马车不断被运粮的牛车、挑担的农人堵住。他也不急,索性下车步行。
道旁的农家小院里,妇女们忙着舂米,石臼发出沉闷的"咚咚"声;孩童们在新米堆里打滚嬉戏,笑声清脆如铃。
城门口,几个老农正围着府衙新贴的告示议论纷纷。
"大人,这是真的吗?新米市价收购?"
叶明点头:"不错。府衙设点收购余粮,价格比往年高两成。"
老农们面面相觑,突然齐刷刷跪下:"青天大老爷啊!"
叶明连忙搀扶,心中却一阵酸楚。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,所求不过是一个公平的价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