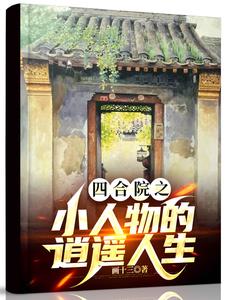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诱局(西子) > 第626章(第1页)
第626章(第1页)
沈怀南言简意赅,“六成。”
许柏承一连嘬了小半截,“以前你出庭的案子几成。”
“九成。”
许柏承没吭声。
青白色的灰烬一厘厘洒在石灰地上,沈怀南脚下是四四方方的瓷砖,大理石折射的光晕终止在水泥地的边缘。
“瞧不上六成胜算?”他嗤笑,“出头控告你的人是黄延祥,金方盛也出力不少,你惹下的十几桩旧债都在这节骨眼爆发了。如果林姝没有求我,我只会踩你一脚,你连一分逃脱的概率都无。”
我距离许柏承如此遥远,距离沈怀南也同样遥远,可我嗅到浓烈的烟草味,它翻滚着,如他们唇边溃散的烟云。我清楚我没有嗅到,它是假的,是我的幻觉。又偏偏真实到呛鼻,放肆地熏缭,燃烧,毁于一旦。
他们手中的烟几乎抽完,许柏承把烟头碾灭在锁住他双腿的横板,“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沈怀南不加掩饰眼中的轻蔑,“和我谈条件,你也配。”
许柏承吐出一团烟尘,“你不妨听一听是什么条件再拒绝我。”
沈怀南原本要离座,他又坐好,“你条件是什么。”
“万一判决结果是余下的四成,我败诉了。”他颤抖着右手,索要第二根烟,沈怀南将烟盒丢过去,许柏承整个人都处于极端的紊乱,他点上烟,“你不是喜欢她吗。”
沈怀南眯着眼,“然后呢。”
“只要败了,我这辈子恐怕再没机会踏出监狱。她和孩子,就依靠你了。”
我攥着拳。
沈怀南似笑非笑,“你倒舍得。”
许柏承并未计较他冷嘲热讽的姿态,事到如今,他没有和沈怀南计较的资本了,“我朝不保夕,拿什么护住自己的女人。”
沈怀南笑容转冷,“你以为你托付我,我能办到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