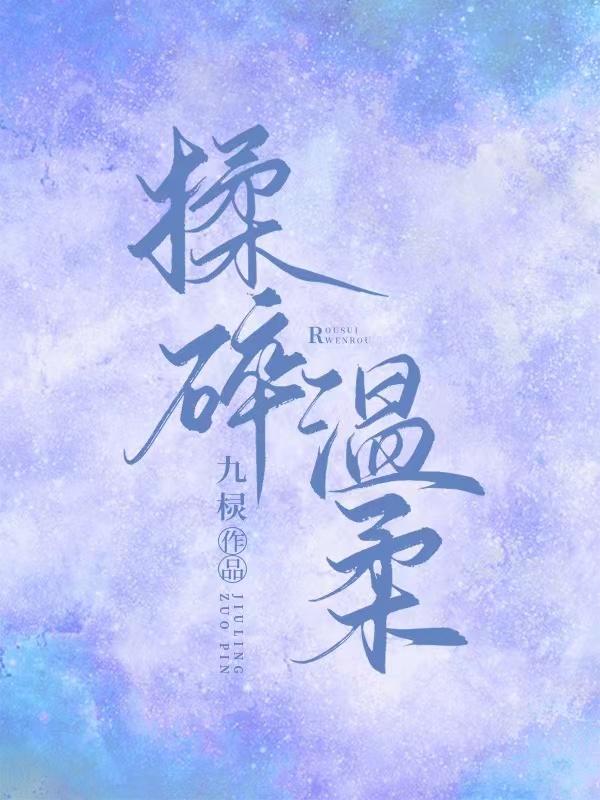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清末小旗兵 > 第481章 我带走了(第2页)
第481章 我带走了(第2页)
几个老人跟在付宁后头也对着那纷纷扬扬的碎屑喊着,直到一切归于平静。
离开墓园一段距离之后,人们把身上的孝服脱下来,用包袱包好了。
要不然,这样的重孝,哪个客栈也不会让他们进的。
老杨早就把抚恤金都分好了,不在付宁这里的,能寄的就寄走了。
拾福峪有九户人家是警卫排的家属,这次都拿到了二十块大洋的抚恤金。
抚恤金的标准付宁不知道,但他知道要是没有黄琛,这笔钱百分之百批不下来。
就算是有,过上几道手,到了家属手里,也就剩下几根毛儿了。
家里的顶梁柱没了,这笔钱就是这些人家将来生活的倚仗。
人们脸上都是悲戚,但是活人还得往前走。
自从《塘沽协定》签了,抗日同盟军散了,各地的战斗差不多都结束了。
买卖铺户渐渐开张了,出门避难的人陆陆续续也回来了,城市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
但这生机里,怎么品,都像是有股死气。
付宁估摸着大福家的人也该回来了,过宣化的时候,把苗诚和苗义都放下了,让他们把这边儿的活儿干完了直接回北平。
赵家庄现在是故事越来越多,单放一个人,付宁觉得不踏实,还是让他们哥儿俩就个伴儿吧,遇上事儿还有个商量。
他们再回到拾福峪,就正好儿赶上了秋收,黄豆、土豆、玉米都该开始排着队的收割了,还有地里各种各样的菜也都快老了。
更别提他们一直干的垒堤堰、垫土、挖水渠了,搁到什么时候,这都是重体力劳动。
繁重的劳动是摆脱一切情绪的法宝。
不管是大喜还是大悲,只要在地里干上一天的活儿,累到大脑宕机,就没那么多时间想东想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