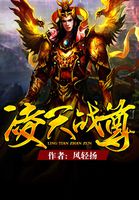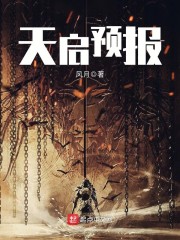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古典白话合集 > 二刻拍案惊奇 卷二十二到卷二十四(第1页)
二刻拍案惊奇 卷二十二到卷二十四(第1页)
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
在这世间,最不懂得稼穑艰辛的,当属富豪子弟。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物,最终也会以不正当的方式失去,这便是天道循环的道理。
宋朝时期,汴京有个名叫郭信的人。他的父亲在宫廷内诸司任职,家境极为富裕。郭信作为家中独子,从小备受娇养溺爱。父母不让他轻易外出,只让他在家读些浅显的启蒙书籍。除了读书,家中大小事务都不让他参与。待到十六八岁时,为了博取名声,郭信在父亲安排下,拜察元中先生为师求学。这位先生在京师的一处僧房开办学馆,环境颇为齐整。郭家便在学馆旁租了三间屋子,虽然幽静,但郭信仍不满意,觉得不够华丽。
他看着屋后的一块空地,决定另行建造房屋。由于郭信既不懂工程预算,也不了解建筑材料行情,全凭家人和工匠随意报账,花费了大量钱财,他也毫不在意。房屋建成后,经过精心装饰,变得富丽堂皇,郭信这才心满意足地住了进去。他每天都让书童仔细打扫门窗梁柱,稍有污渍,就要求匠人连夜更换,否则心里便不踏实。
在穿着方面,郭信只穿新衣服,穿上后还要反复打量,稍觉不合身,就重新购置衣料制作。鞋袜也必须是上好绫罗材质,一旦沾上污渍,立刻丢弃换新,洗过的衣服更是不愿再穿。
当时,有位赴京听候调职的黄德琬官人,他的住所与郭家相邻。看到郭信如此挥霍,黄德琬心中很不以为然。后来两人熟络起来,黄德琬常常好心相劝:“你年纪轻轻,不了解世间生活的艰难。钱财来之不易,虽然你家境富裕,也不该如此浪费。长此以往,就算家底再厚,也有耗尽的一天。到那时,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”
郭信听后,在心里暗自嘲笑:“尽是些寒酸之言。钱财哪有用得完的时候?我家田产数不胜数,怎么会有入不敷出的情况?不过是因为他们家里没钱,眼界狭窄,才说出这种话,根本不懂我们富家的生活方式。”他把这些劝诫当作耳旁风,依旧我行我素。黄德琬见劝说无用,深知这是被娇惯坏了,心想:“且看他日后会有怎样的下场!”后来黄德琬得到官职,离开京城,此后两人便没了音信。
五年后,黄德琬因事再次来到京城,打听旧邻居郭家,却发现早已没了郭家的踪迹。偌大的京城,也无处可寻。一天,他偶然去拜访一位名叫陈晨的亲戚。主人还未出来,先由门馆先生出来接待。只见一个人衣着邋遢、无精打采地踱步出来,仔细一看,竟是郭信。他戴着破旧的头巾,穿着褴褛的衣服,手臂颤抖着施了一礼,然后在椅子上坐下。
黄德琬见他满脸饥寒交迫的神色,心中不忍,关切地问道:“你为何会在这里?又为何落得这般模样?”郭信长叹一声:“谁能想到会这样?钱财要没起来,根本不用等花完,一下子就没了。”黄德琬追问缘由,郭信说:“自从与您分别后,父亲不幸离世。后母在守丧期间,卷走了家中所有财物,回了娘家。第二天再去打听,连她的家都搬走了,不知所踪。家里的仆人也纷纷四散逃走,只留下我孤身一人,一无所有。幸亏还识得几个字,只能在这家教小学生勉强糊口。”
黄德琬说:“家财没了,还有那么多田产,这些是偷不走的。”郭信无奈道:“平日里我根本不知道家里有多少田产,也不清楚田产在何处。父亲一去世,田产账簿也不见了,如今我连一亩田都不知在哪里。”黄德琬又问:“当初我好心劝你,你还记得吗?”郭信懊悔地说:“那时候,见到东西就买,哪管钱是怎么来的?只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。听到说要节俭,根本不明白有什么好惜的。哪里想到如今会连一文钱的来路都没有!”
黄德琬问:“你现在在这里教书,每月收入多少?”郭信说:“能有多少?每月一千文钱,连维持生活都不够。只求能勉强糊口,不用为柴米发愁就不错了。”黄德琬感慨道:“你当初一天的花费,就抵得上现在一年的教书收入。富家子弟沦落到这个地步,真是可怜!”他身上恰好带着几百文钱,便全部送给郭信,以表故人之情。
不一会儿,主人出来,黄德琬又向主人讲述了郭信曾经出身富贵的经历,叮嘱主人好好对待他。郭信感激不尽,捧着几百文钱,如同得到珍宝一般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,继续回去守着那冷清的教席。
想想看,当初郭信富贵时,几百文钱给人赏赐都觉得不痛快。如今才知道钱财的珍贵,却为时已晚。这都是因为他幼年时不知生活艰辛,才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,他能在此时明白钱财的重要,也还算有些福气,这便是人们常说的“败子回头好作家”。
接下来,再讲一个败子回头的故事。浙江温州府有个姚姓公子,他的父亲官至兵部尚书,岳父上官翁也是位高权重的官员。姚家世代富裕,积累了巨额财富,方圆百里内的田圃池塘、山林川泽,几乎都是姚家产业。姚公子父母双亡,又没有兄弟,独自掌管家中事务。妻子上官氏生性温柔寡言,从不干涉外事,因此家中大小事都由姚公子随心所欲地处置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姚公子自恃家境富足,养成了奢侈挥霍的习惯。他喜欢结交那些不务正业的朋友,这些人用言语奉承、哄骗他,说自古豪杰英雄都不事生产,行事慷慨,不把钱财放在心上,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才称得上侠烈之士。姚公子年轻气盛,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,牢记于心。看到别人家精打细算、经营家业,他就认为对方是斤斤计较的小人,不屑一顾。
姚公子懒得读书,也不准备参加科举考试,一见到文人墨客,就脸红心跳、手足无措,满心厌烦,远远躲开。他身边整日围绕着两类人:一类是能说会道、善于阿谀奉承的人,姚公子一天都离不开他们;另一类是勇猛强悍、喜欢炫耀武力的人,姚公子与他们相见便兴致高昂,交谈时情绪激动,行事也变得风风火火。只有和这两类人,姚公子才有共同话题。
在这两类人的引荐下,许多市井无赖纷纷前来依附姚公子,他们各展所能,讨好卖乖。姚公子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豪爽,不论对方人品如何,一概接纳。他身边前呼后拥,跟随的人足有上百人。这些人不仅靠姚公子供养,每人还要拿安家费和每月的衣粮。姚公子对此毫不吝啬,看到他们拿着钱回家,心里反而觉得痛快。
姚公子喜好射猎,钟情于骏马良弓。有门客说某处有一匹名马,价值千金,能日行数百里,姚公子便立即如数支付银两购买,从不计较价格高低。等马买回来,只要毛色好看、身材高大些,他就觉得值了。要是有人说买贵了,他反而不高兴,只有听到别人夸赞买得便宜才开心。大家摸透了他的脾气,只要他买东西,就一味地赞美。遇到有人推荐良弓,姚公子也是如此。
门下的人为了从中获利,又为了迎合姚公子,陆续买下好马一二十匹、良弓三四十张。姚公子挑选一匹最喜欢的时常骑乘,其余的任由门客使用。他常与门客相约,各自骑马持弓,分路出发,约定在某处会合,先到者有赏,后到者受罚。赏赐的钱财大多出自姚公子,惩罚也不过是罚酒。通常都是姚公子先到,众人罚酒,还会用大酒杯向他祝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