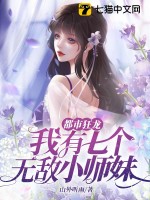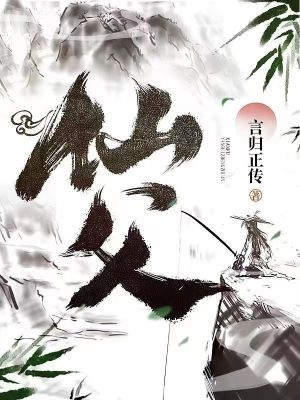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逆天北伐:姜维铁蹄踏破魏都梦 > 第166章 沓中屯田护民生(第3页)
第166章 沓中屯田护民生(第3页)
木盒里装着曹髦的血书,“司马昭弑君”四字的“弑”字少了一笔,显然是临终前力竭所致。血书背面用金粉写着:“朕子曹霖,望将军护其西归,重振大魏。”姜维望着少年眼角的朱砂痣,想起相术上说“痣在眼角,命带贵气”,竟与当年刘备初见诸葛亮时的记载暗合。
“公子可知,”姜维低声说,“蜀魏之争,实为汉贼不两立。今司马昭弑君,天下共愤,若公子以汉室宗亲之名……”他突然住口,意识到自己差点说出大逆之言。曹霖却点头:“将军毋需忌讳,父皇临终前说,唯大汉丞相后裔可托孤。”他摸出一枚玉佩,上面刻着“亮”字,正是诸葛亮当年赠给曹髦的见面礼。
五更梆子响时,姜维带着曹霖混出洛阳城。城门卫兵检查时,姜维故意让冰稻种掉出几颗,卫兵们哄抢着去捡,没注意到少年僧衣下的玉佩反光。青骓马踏上官道时,姜维回望洛阳城头,看见瞎眼琴师站在垛口,手中的琴弦已断,却仍在比划“快走”的手势。
第四折 阴平古道埋玄机
四月初八,阴平古道的石阶被春雨泡得湿滑。姜维牵着曹霖的手,看着少年被磨破的鞋底,想起自己十二岁时随父出征,也是这样磨破了三双鞋。阿莱娜给的冰稻种只剩小半袋,他每隔一里就撒下一颗,蓝色的稻种在青苔间格外显眼,像一串永不熄灭的灯。
“将军,”曹霖指着远处的悬崖,“那里好像有字。”姜维望去,只见崖壁上刻着“汉德昭昭”四字,笔画间长满了青苔,却在雨水冲刷下露出底下的朱砂——那是诸葛亮北伐时留下的标记。他摸出武侯剑,剑柄与刻字共鸣,竟在崖壁上照出八阵图的虚影。
申时初,暴雨倾盆而下。姜维带着曹霖躲进山洞,却见洞内堆满了腐朽的木箱,箱中装着锈迹斑斑的弩箭,箭杆上刻着“诸葛”二字。他突然想起,丞相曾在《后出师表》中提到“祁山、陈仓、阴平,皆有藏兵洞”,眼前的弩箭,正是二十年前街亭之战时的遗物。
“公子,”姜维捡起一支弩箭,箭头的三棱形设计与他改良的连弩一模一样,“此乃武侯连弩的原型,当年丞相令马谡守街亭,曾在此处藏弩三千。”曹霖抚摸着箭杆上的刻痕,忽然说:“父皇曾说,诸葛亮是‘大汉最后的守护者’,今日一见,果然如此。”
深夜,洞外传来马蹄声。姜维吹灭火把,武侯剑在黑暗中泛着微光,那是剑鞘里的熊爪图腾与他的血脉共鸣。曹霖握紧木盒,指节发白,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:“将军,若我被俘,便说是西域胡商之子,您只管快走。”姜维按住他的肩膀,感受到少年身体在颤抖,却仍挺直了脊梁。
来者是邓艾的斥候,打着“搜捕刺客”的旗号。姜维用西羌语大声咒骂,假装被惊醒的胡商,怀里的冰稻种适时掉出。斥候们见是西域货物,又闻到浓重的羊膻味,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曹霖望着姜维脸上的胡商妆容,忽然想起洛阳街头的说书人,曾讲过“姜维诈降”的故事,此刻方知,忠义之人,何止能战,更能忍辱。
五更时分,雨停了。姜维带着曹霖继续前行,阴平古道的悬崖上,偶尔能看见野山羊跳跃的身影。曹霖指着一只白山羊,说它像极了洛阳太学里的“瑞兽”画像。姜维笑了,说:“在西羌,白山羊是吉祥的象征,若你到了沓中,阿莱娜会用羊奶煮青稞粥招待你。”
第五折 沓中重逢定乾坤
五月初五,沓中平原的麦子熟了。姜维站在“生门”指挥台,看着阿莱娜带着羌人部落的车队归来,车队里不仅有粮食,还有数百名曹魏逃兵,他们的甲胄上,“魏”字被划掉,换成了用炭笔写的“汉”。曹霖望着这场景,忽然明白,真正的征服,从来不是靠刀剑。
“伯约,”阿莱娜递来一碗冰稻粥,粥里混着野蜂蜜,“老祭师说,冰稻亩产十石,足够支撑十万大军。”姜维接过粥,指尖触到碗沿刻着的狼族图腾与汉字“姜”,这是阿莱娜特意为他烧制的陶碗。远处的屯田兵们正在收割麦子,他们哼着陇右民谣,调子竟与诸葛亮的《梁甫吟》相似。
曹霖蹲在田垄间,好奇地捏起一颗冰稻粒,蓝色的米粒在阳光下透着晶莹:“这稻子真的能在雪地里生长?”阿莱娜点头,用西羌语说了句什么,旁边的羌人少年立刻捧来一碗酸奶,碗底沉着几颗冰稻。“诺敏改良的品种,”姜维解释道,“用西羌雪水和汉军的屯田肥,三年才成。”
申时初,沓中幕府内,姜维展开从洛阳带来的密诏与地图。曹霖看着地图上用朱砂标记的“许昌”“长安”,忽然指着陈仓道:“此处曾是父皇与郭淮密谈之地,地道错综复杂,或许能藏兵。”姜维的武侯剑“当啷”落在地图上,剑尖指着陈仓:“正合我意,当年丞相在陈仓藏过连弩,如今该派上用场了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阿莱娜突然推门而入,手中握着狼族的“千里传讯鹰”,鹰爪上绑着染血的纸条:“钟会在成都大肆屠杀,百姓们自发组织护汉旗……”她的声音哽咽,狼骨耳坠轻轻颤动,“诺敏的冰稻田,被魏军烧了一半。”姜维起身,按住她的肩膀,却发现她肩头有箭伤,血迹已浸透胡服。
“他们用了‘阴魂蛊’,”阿莱娜掀起衣袖,露出手臂上的紫黑色纹路,“中者七日之内化作行尸走肉。”曹霖倒吸冷气,想起洛阳街头的“鬼甲军”传说,那些士兵的瞳孔也是这般颜色。姜维摸出老祭师给的“驱蛊草”,嚼碎后敷在伤口,绿色汁液与紫色纹路相触,竟冒出青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