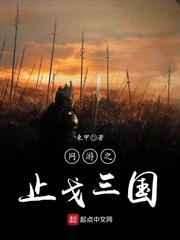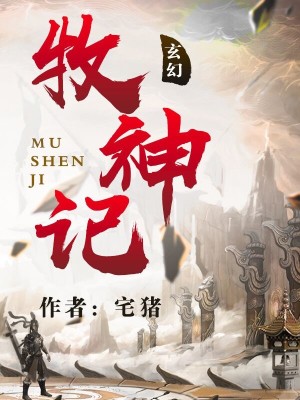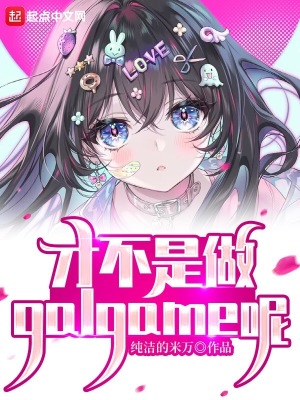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岐黄手记 > 第351章 手稿定稿·祖父的题字(第1页)
第351章 手稿定稿·祖父的题字(第1页)
雕花木窗的格纹把晨光切成细碎的菱形,落在苏怀瑾摊开的手稿上。最后一页《铜药碾的传承》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,她指尖划过末尾那句“三百年的铜药碾,要碾出适合现代人的方子”,忽然想起昨天陆则衍帮她校稿时,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铜碾轮,标注“就像这个,既要转得动老药材,也要碾得碎新问题”。
“咔嗒”一声,枣木拐杖敲在青砖上的声音从走廊传来。祖父穿着藏青色的绸衫,袖口挽到小臂,露出常年碾药的手——指腹有层薄茧,虎口处留着铜药碾磨出的浅痕。他手里捏着支狼毫笔,笔杆被盘得发亮,砚台里的墨是刚磨的,泛着淡淡的松烟香。
“拿来我瞧瞧。”老人在书桌前坐定,老花镜滑到鼻尖,他也不推,就这么眯着眼逐页翻看。手稿堆得整整齐齐,每章都夹着不同的书签:“肝郁气滞”章用当归叶,“痰湿体质”章用陈皮,“气血不足”章用红景天——都是苏怀瑾从药材标本里挑的,说“这样翻起来就像闻着药香”。
翻到“老顾的多系统萎缩”那页,祖父的手指在“附子理中汤加减”那行停住了。他眉头微蹙,指腹在纸页上轻轻敲了敲:“这里少了句根。”他抬头看苏怀瑾,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浸了水的墨石,“老顾是‘寒邪困脾’,你用附子理中汤没错,但得告诉读者‘为什么这么用’——《伤寒论》里‘自利不渴者,属太阴,以其脏有寒故也,当温之,宜服四逆辈’,这才是方子的根。”
苏怀瑾赶紧抽了支笔,在空白处补写。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里,祖父又翻到“小周的肝郁调理”,看到“疏肝茶包(柴胡6g+陈皮5g+玫瑰花3g)”下面,陆则衍附的心率变异性数据对照表(干预前后自主神经稳定性提升23%),嘴角悄悄松了些:“这样好,中医说‘疏肝理气’,西医说‘自主神经调节’,两相对照着,懂行的、不懂行的都能看明白。”
等看到最后一页的结尾,祖父把手稿往中间推了推,蘸了墨。他手腕悬在宣纸上方,指节微微用力,墨汁在笔尖凝了个小珠——这是他碾药时定准药材分量的习惯,落笔前总要先“稳住气”。“守正创新”四个字先轻后重,笔锋像老树根扎进土里,“守”字的竖钩带着韧劲,“新”字的点画又透着灵劲,最后添上“方为传承”,四个小字稳稳托住前面的厚重。
末了,他从砚台旁摸出个小巧的朱文印章,蘸了朱砂,在落款处轻轻一按。“苏氏仁济”四个字方方正正,印泥在宣纸上晕开极浅的红边,像给这行字镶了道暖边。“这才是书的魂。”祖父放下笔,看着墨汁慢慢渗入纸纤维,“方子能治病,是本事;能说清‘为什么能治病’,让后人学得来、传得下去,才是传承。”
“爷爷!瑾姐!”赵小胖举着手机闯进来,镜头还对着院子里的药圃——研学班的孩子正在认薄荷,丫丫举着标本喊“这个能醒神”。他把镜头转过来,对着祖父的题字:“刚直播说手稿定稿了,网友催着看封面呢!我觉得爷爷这字比设计公司给的字体有力量,能不能当封面?”
直播间的弹幕瞬间涌了上来,像煮沸的山楂水:
“这字有筋骨!‘守正’两个字沉甸甸的,‘创新’又透着活气,像铜药碾碾药材——又稳又有劲儿!”
“终于明白瑾姐为什么能写出这本书了,爷爷的字里就带着‘老规矩里有新办法’的意思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