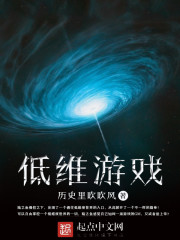笔趣阁 > 《盘臣》作者:旷宇 > 第249章(第2页)
第249章(第2页)
“邢昭……”
成帝声音沙哑,唤他一声。
“靳王今日执兵入宫,既不唤‘符玺郞’,究竟是何目的,说来听听罢。”
成帝适才听闻靳则聿扣押了两名皇子。
彼时出于帝王至尊,便不能开口“谈条件”
一开口便是全然地示弱,成帝一直在寻时机。
此时邢昭所为,不啻于对靳则聿的“反戈一击”,成帝开国之君,对“稍纵即逝”四字之把握,洞入骨髓。
靳则聿凝视着成帝,又仿佛不在凝视着他,像是在这四方宫殿中凝视着莽莽乾坤。
他一字一顿:
“我心中所念,并非关于他人,时常也非关乎陛下,若说关乎天下生灵,也未免托大,只是知行之间,我当作何为,不违己心,作为‘人臣’,我再退一步,向陛下提请,北藩于边,若陛下再欲赶尽杀绝,我便要有一些不敬之为了。”
靳则聿说着,从腰间解下那枚‘人乘龙’佩,示意了成帝身旁的公公。
黄绿相间的配饰在他一抬手之间,流动出一种姿彩,与此时的气氛殊异。
那公公虽也受了些惊吓,但机敏犹存,不知从何处托出一个盘来,接了过去,奉至成帝面前。
成帝收了那佩,端详目前,问:
“不敬之为是指?”
“届时陛下自然知晓。”
靳则聿今日应对异常干脆,且丝毫不掩机锋,接着说道: